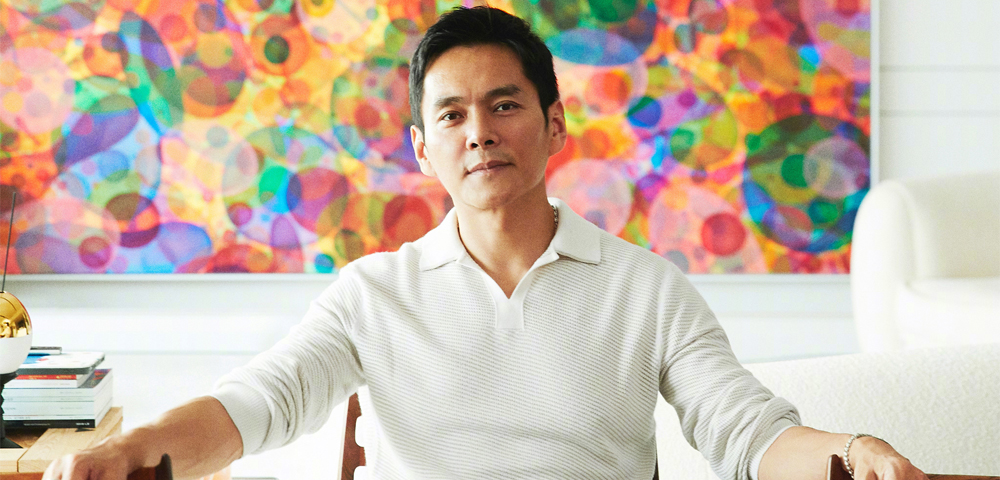曾美慧孜
曾美慧孜曾在话剧《日出》里演“小东西”,一个孤苦无告、不堪被蹂躏和毒打的女孩儿,每每演到“小东西”结环自尽的那一幕,曾美慧孜心里总会涌起一种激动:身为演员,死也要死在舞台上。
长大后她明白,把这样的结局视为表演的终极定义有点极端,但也更加确定,自己可以为表演奉献一切,一种宿命式的、信仰般的坚定。她知道冥冥之中自己必然会遇到一个不同的角色,“所以当它真的发生时,也不会感到意外”——在电影《三夫》中扮演的“小妹”,让曾美慧孜被第55 届金马影展和第13 届亚洲电影大奖提名为最佳女主角,并最终在第38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影后。
潜意识里她一直在等待这个角色的到来。她对表演的狂热和信念中,当然包含着自我成就的欲望,她也曾暗自惆怅,这是否只能是一种执念?

曾美慧孜
当众孤独的安全感
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曾美慧孜都曾不知所措。
“当时还不知道电影职业本质的核心,也没有让自己的表演和社会理解力更扎实的基础,所以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导演甚至曾美慧孜自己,一度都很难从外形上把她归入某个合适的角色范围里:一张娃娃脸,却已经拥有成熟女性的身材曲线,如果角色并非恰好需要这样似是而非的过渡阶段,她便陷于两端不靠的尴尬境地。
这不是身体第一次让她感到困惑。小时候她比同龄人发育得早,发现自己的身材在一群扁平如柴的女孩子里犹如鹤立,她只感到害羞,并试图隐藏:她不愿意穿胸衣,下意识驼背,以为这样可以隐入更多人中间。童年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周围被称为“我们”的所有人,往后的人生步伐仍会保持高度一致,无论是样貌身材还是思考方式的“与众不同”,最初往往伴着隐秘的羞耻感,因为它迫使你离开安全的大多数,并用一个问题步步紧逼:“你是谁?”
这个问题并非如一支尖锐的刺突兀而出,但隐隐约约间,她能感到它如影随形。她成绩并非拔尖,自觉永远都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已经习惯了对自己的失望。一次在学校上讲台演讲,突然间,她自以为的自卑、孤僻和不善表达全都消失不见。“那时是释放的,完全不感到害怕。”这让她找到了支点,被众人观看的时候,她会变成另一个人,她需要一盏聚光灯。
“我非常迷恋那种当众孤独的感觉,让我特别有安全感。可能这也是后来我非常坚定自己适合成为演员的原因。”
成为演员是她11 岁时就下定的决心。被导演娄烨选入电影《颐和园》,又被导演李玉选入电影《苹果》,看起来起跑线被镀上金光,梦想即将扬帆起航,可她却停滞在了那个起点上,没有更大的力量让她冲上更高的台阶。不是没有角色演,但她很清楚,那些并不是内心真正的渴望。
黏稠而漫长的等待里,她也曾想过,自己是否不是那块料?小时候她学舞蹈,转圈永远做不到其他同学那种饱满和利落感,母亲劝她,放弃吧。“我没有放弃,可结果是我仍然转不好。”一度她以为是身体曲线作祟,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差一点转圈的天分。这一回是否会重蹈覆辙?暂时没有答案,但想来想去,她没法动摇一直以来的坚定:“我真的喜欢电影。”
那几年里,沮丧和打击已经变成日常。“每天灰心,每天坠落一次,每天有90% 以上的部分都不如意,可能那剩下的10% 不到的一件事会让你像吃了糖一样。”
她也去见过不少经纪人和相关人员,可发现自己并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就只能一个人拎个包继续去健身房,这是实际能做的,就是尽量对自己好一点。”
她想努力过好日子,先让普通意义上的“生活”踏实。她觉得自己过得“不像个演员”,早上看书,下午健身,晚上看碟、睡觉,规律到近乎严谨,“像个理科生”。为了一个角色的准备,她曾跑去给自己的编辑朋友当服装助理,帮着给其他拍摄对象挽裤腿烫平褶皱。“那也是一个抽离的过程,就是我可以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待我的职业,更明白每个角色的艰辛,也积累了创作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找不到方向,她干脆去纽约进修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刚去的时候,英语只够基本交流,同学们讨论到艰深一些的专业理论,她就插不上嘴。她住在新泽西,每天晚上回家要坐长长的一段地铁,月台是空的,车厢是空的,她的心也是空的。
去美国前她曾疑惑过,书上讨论的那些电影理论真正存在、并且可以付诸实践吗?“我在学校看到了真正的体验派、方法派,每个派系都有人在讨论,而且会自我分辨和归类。”虽然在那种冲击下她并没能立刻做到自我的精准定位,但回国后重新进入剧组,她有了更平实的心态:一切可以重头开始。

曾美慧孜
先做一株扎进土里的草
回国后她演的第一部戏是电影《冥王星时刻》,也是她第一次真正扮演了一个成人的角色。“那时我觉得自己真正是个女人了,那种能量非常强大。”
在时间悄无声息的缝隙里她完成了成长,也在一些前辈身上看到了可能的前行方向。“比如梦露,她也是娃娃脸和成熟女人身材的结合,而她一生的悲剧色彩,让她的那些喜剧有了抽离感和对立性。又比如巩俐,她非常有生命力,表演有节奏有气味,如果不是勇敢地去突破一般人所认知的范围,不会有那种‘湿漉漉’的感觉。”
她们虽然是女神级的人物,却都拥有一种浑然天成、在土地里扎根的力量感,这让曾美慧孜震撼和着迷。她知道自己表演的优势,中学时她就拿下过全国级别的主持人比赛奖项:“我的声音条件不错,说台词会有‘戏’的感觉。”她也知道自己的缺点:“以前技巧不够好,只能来真的,要我来20条我就只能来20 条真的,会虚脱掉。现在我会更关注周围的节奏,让所有人都舒服一些。”
一开机,她就觉得自己成了某种生长在魔域的生物,“突然间手心都会睁开眼睛”,各种平日里从不显山露水的情绪都会出现在她的角色身上。“好像各种神兽上身。有时我会吓到周围的人,居然会在现场调动出这样的东西来……表演是巫术,人就是那么有趣的动物,比想象中天真,比想象中黑暗。”
认识曾美慧孜许久的朋友曾说,她就是日本电影《大逃杀》里那个最后抱着娃娃出来的人。“他们从来没看到过我发脾气,也从来没看到过我冲动。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放在了角色里,所以我抵达和冲破角色的极限时,是毫不费力的。”
但奇妙的是,她未曾遇上过“无法出戏”的问题,成为一个“稳定的人”,是她表演的一种助力。“演戏时我的确是‘不疯魔不成活’,但在那个瞬间我就可以找到平衡点,然后回到日常的自我状态。”她的父母从事科研方面的工作,凡事要讲理、有据、重逻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她习惯用更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
“妈妈一直说,人主要是靠分子结构裂变,还有它的摩擦力,裂变完成后,你要迅速回到原子核和分子核的稳定结构。她还说,只要能控制分子裂变的节奏,控制多巴胺这些体内的化学元素,就可以控制你自己。”

曾美慧孜
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曾美慧孜根本来不及细想表演和真我之间的距离问题。“生活本身已经大过了一切,每天只求好好活着。”但这种磨练也让她更珍视“地气”,回国后,她没有安排经纪人也没有助理,觉得这样更尊重效率。“为什么不在精力旺盛的时候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呢?这些事情也能让我体谅每一个部分的工作,我想成为一个更强的人。”
她想规避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危险。“我想成为一个可以塑造生活百态的演员。我必须先成为一株扎进土里的草,才可以演一棵参天的大树。” 所以她有足够的耐心。“我觉得一些角色不是仅靠争取就能得到的,我要准备到一定的阶段。可能我要得到一个结果,就要比别人辛苦一点。”
导演毕赣看了一张曾美慧孜的照片,都没见面,就定下她演《地球最后的夜晚》。导演陈果见曾美慧孜第一面时只一起喝了杯咖啡,也没说戏,她还以为导演对自己不满意,谁料过几天再约她见面,一上来就直切主题,开始讨论《三夫》的拍摄细节。“我还没准备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切就发生了。”
她想,生命中的一切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她等待了十几年,已经习惯了黑暗。“所以见到光明也不会太过狂喜,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还需要些时间,一切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孤独给了她某种自信。“孤独的时候人会比较清醒,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短板,也会慢慢明白,不要去‘冲’这块短板,人都是不完美的,朝另一个方向努力,这块短板可能会成为成功的另一块基石。”
如今,外在身体和内在思想的成熟度终于统一,真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距离已经平衡,她可以更坦诚地面对自我,直面所有的欲望、自在的表达。“我对欲望最初的认识来自一句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的极致是空性的,而抵达空性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五彩斑斓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