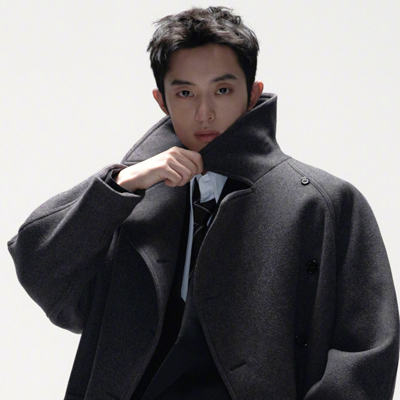刘擎
伴随东亚社会的女性主义觉醒,千禧年前后掀起的、对“浪漫爱” 的热望与追求逐渐冷却,“为爱成婚” 模式成立背后被隐藏的结构性问题和性别不平等开始被重新审视,一度以“爱情至上” 而风靡的文艺作品成为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解构、玩梗的嘲讽素材,在今天,我们要如何重新想象爱情?或者说,爱情仍旧是一个值得花费精力探索、学习的课题吗?
刘擎的答案仍旧是肯定的,四年前他在一档谈话节目中发表的,对于爱的定义—— “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 在社交媒体上创造了9000 万的流量奇迹,至今仍旧在被转发。这让他相信,爱情仍旧是每个平凡个体在有限的人生体验中所能创造出的最大奇迹,无关事实理论,只关乎个体经验与价值判断。
而“爱”作为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不仅关乎异性之间的浪漫爱、激情之爱,也涵盖更大意义上人类之间流动的、美好的交互关系与情感,以及在“孤独社会” 中逐渐稀少的人情味和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而他想做的是,从爱情出发,在“关系凋零”的现代社会对抗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刘擎
Q&A:
为什么会在这个流行“爱情祛魅”的网络语境下重新讨论爱情?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刘擎:有两个原因吧。一是2021 年5月我受“道长”梁文道邀请,在小红书的一个对谈节目《角落的夜晚》中探讨爱情,引用了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观点—— 爱是最小型的“共产主义”,另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爱情能让一个凡人得到最高的承认。这个切片的不同版本在互联网引发了近一个亿的转发,后来就又不少人提议,希望我比较系统地探讨爱情这个主题。
第二个原因是,我所专注的哲学和政治学通常被认为跟生活无关,但其实政治学最根本的关切正是关于人们如何生活在一起,关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而最小单位的共同体就是亲密关系,它也是政治哲学领域的微观细胞。
以上这两个动因让我想看看,“亲密关系”这个领域能不能从哲学的视角来重新探索。当下大家特别注重条件选择,在这种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诞生了“婚恋市场”的说法,以“车、房、年薪和情绪价值”作为指标将爱情换算成一笔供需关系的交易活动,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只有这一种?
我在对“现代性”问题的相关讨论中谈到过,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他认为,现代社会存在两种逻辑,一种是“系统”的逻辑,由本利计算的工具理性主导,一种是“生活世界”的逻辑,基于人与人爱、信任和关怀。但现代性的发展有一种趋势,就是工具理性越来越强大,不断扩张,导致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很深地侵入到爱情领域,这本该是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关系领域之一。这意味着现代人的异化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所以,阿兰·巴迪欧认为,捍卫爱情是哲学的一个使命,是我们用以抵挡生活世界最终沦丧的一种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从哲学的视野探讨爱情,是因为爱情作为独特的人类活动本身值得探究,同时,我是想尝试,在今天爱情是否还能够成为一种力量,来对抗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因此,它既是学术性的思考,又是对现实生活的关切。
这听起来似乎是非常理想化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浪漫爱”以及其代表性文艺作品,例如琼瑶系列被社交网络大量结构、玩梗,同时以曲曲为代表的“情感导师”大行其道的、非常撕裂的阶段,这本书有可能给出一个这两级中间的理性解法吗?
刘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我的基调可能是中道的,在理解现实中守护理想,但我的主要目标并不要提出什么解法,不是去调和理想和现实的紧张。我着眼于解释现实何以如此,分析流行话语如何建构了我们的现实感,更重要的是,重新揭示被流行话语所淹没的爱的潜在价值和意义。
我们知道,在人类这四种关系型的活动,性、爱情、婚姻和生育,存在某些复杂的关联,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可以分离的。爱情是一种独立的活动领域,可以脱离婚姻、生育,甚至可以脱离性爱而存在。爱情是两个个体之间由于强烈的吸引进而达成的生命的深刻联结。爱情可以达到双方身心和心灵的总体关系,是其他任何情感和关系都难以替代的。这种全面的关系,也意味着深度的相互袒露会使自身无比脆弱,因此是高风险的,但这种不设防也会创造一个非常奇妙的状态。人们在好的爱情关系中可以获得一种彼此不分的生命共同体状态,这是违背本能欲望的倾向,让“投入”和“回报”的工具理性逻辑在此失效,这正是爱情最美妙的地方。
现在许多人声称现在年轻人都对爱情“祛魅”了,也许是的,也许情况更复杂了。有一部分仍旧对爱情怀抱理想,但认识到现实中遇到美好爱情的概率很低,变得冷静但保持开放的心态。还有一部分曾经投入爱情,经历过挫败和伤痛,其中有些人就宣称爱情根本不存在,都是欺骗或幻觉。说得好像自己把全世界的爱情都谈过了,可以做出这么强的断言。大概是某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这样宣称比较能够安抚自己吧。挫败和幻灭的声音很喧哗,造成了“反向的幸存者偏差”。但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愿意体验爱情的甘苦,并在其中发现自己和世界,获得成长甚至幸福。他们往往比较低调安静,少言寡语,是“沉默的大多数”吧?也许不占多数,大概有一半人吧。
为什么爱情成功学流行了这么多年,年轻人在婚恋问题上还是很惶恐、迷茫的?为什么用交易的方式来展开对爱情的想象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陷阱?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这些,我想让大家重新来看待爱情,把被遗忘、被埋没的可能性及其对生命的意义揭示出来。
这种普遍的功利性论调是不是在东亚更严重,跟文化、社会制度是不是有关联的?
刘擎:全世界都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几乎所有生活领域都被“绩效化”,如果回到家里还是这样,这个世界多荒凉?
现代生活它一定需要系统的逻辑,不然无法运转这么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但是如果全部用这个逻辑,真的是非常可怜,人生活的会很可怜。
近几年的影视作品,尤其是韩剧和台剧,内地也有《好东西》这样的作品在颠覆上世纪下半页“浪漫爱” 叙事和婚恋观念、探讨亲密关系多样性的作品,它们是否在当下提供了更多样化的亲密关系的理解角度和关系的范本?如何看待当下爱情模式的复杂性?
刘擎:是的,《好东西》以及邵艺辉老师本身,对爱情态度仍然是开放的。
事实上,爱情跟婚姻结合在一起,“为爱成婚”是从西方浪漫主义开始的。爱情和婚姻本来是两回事,婚姻是经济、法律、生育合作的一个制度,是要求稳固性的,爱情是两个人的情感,是充满不稳定性的。
浪漫主义在五四时期进入中国,“婚恋一致论”在女性意识尚未觉醒的阶段也经过了看似稳定的实践。但在女性开始改变的当下,这样的模式就遭遇了挑战。上一辈人的婚姻掩盖着很多的性别不平等,不要去美化女性那种不得已的隐忍。我认为像《好东西》这样的作品,它揭示了在什么样的形态下好的爱情是可能的,女性和男性要共同打破不平等关系当中维系的那种温情。
电影《HER》描述的故事就发生在2025 年,部分取景也在上海完成的,我们离剧中描写的人机恋好像只有一步之遥了,您如何看待这种关系的利弊?是否在人们对传统叙事的“爱情” 祛魅,对性、爱、婚姻完成分离之后,这会是一种更加纯粹的感情?
刘擎:是的,前天我就在跟有关的团队开会,AI 情感伴侣已经开始生产了,他们找了4个创业者和4个学者一起来讨论人机恋的未来前景。但是这是孤独的爱,或者叫孤独的性。他和性爱玩具是一样的,是高级的性爱玩具,是完全可以满足你自己的,但是你明明知道他不是另外一个主体。
就是因为另外一个主体太稀少了,难度太大了。
刘擎:所以你是相信它难还是相信它不存在?
在爱情这件事情上,你要相信才能遇到,才能看到。
这种美好的确变得越来越稀缺了,但还是有大量的存在,只是他们没有发声,而我只是为这些幸存者找到一个话语论述的方式。
在经济急速发展了30年之后,近一两年在80、90后这两代急速发展的亲历者当中兴起了“中式梦核”、“县城美学” 这样的亚文化浪潮,以艺术家黄河山为代表的人们开始怀念90年代尚未大规模开发的城市(县城)面貌、居住形态、依托于“附近”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交模式,您如何看待这种迫切的、回到线下的现象?
刘擎:这些都是征兆。
为什么我们怀念“ 附近”?
过去几十年,过度追逐“指标”的阶段让小镇做题家离开小地方、离开熟悉的“附近”,但钱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在今天,我们还是会被社交媒体上在夜市摆摊的小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感、在医院这样的公共场所礼让他人、释放善意的举动打动。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是很动人的,在我看来这就是对“附近”的一种重新找到,也是关于如何在陌生人社会将小共同体的情感进行扩展的一种示范。
从这个层面去看,其实爱情的凋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折射出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凋零。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说,“你要按自己想象的生活,否则的话你只能按照自己的生活来想象”,我们现在活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既定的生活模式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你可以将这本书、这门课看作我发出的一个邀请,当然如果游戏世界、人机恋能够解决,能够让你感觉不错,不需要谁来做什么启蒙,that's fine。这个世界不需要老登,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目前的现状还是有迷茫,你也愿意尝试和探索,那我们一起来想象新的可能。
策划:李祺 / 采访、撰文:李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