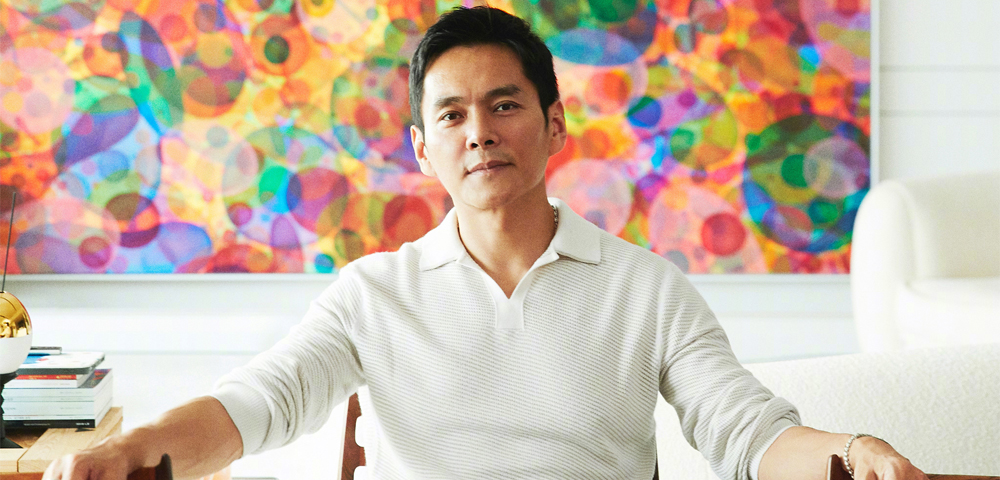叶锦添
我曾经想过只做电影美术的,但我发现电影好像追不上我们成长的速度。现在市场已经大量地被商业电影覆盖,娱乐成分太多了,非常少数的电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电影,所以我们拼命想做的已经不是大众最想看的那种电影了。
我常常处于一种“我很有天分,但是没有做到最好”的状态,蛮浪费时间的。我一直觉得绘画是我的事业,小时候就喜欢画画,但是又不画那种正统的画。香港的文化是很世俗化的,比较缺少想象的、很飞很high的部分,我对香港的主流文化没什么兴趣,我也知道香港主流阵营对我的画大概也不会有兴趣。我的家人也很担心我做艺术会没法生存,所以他们也不许我学画画,希望我不要变化太大。
但我开始做电影美术,反而就是因为我会画画。念大专的时候,有一张我几年前画的很早期的绘画作品拿了很大的奖,画那幅画的时候我是想当画家的。就因为这个奖,吴宇森导演的 《英雄本色》找我去做电影美术。
拍完《英雄本色》,我感觉自己迟早会被砍死。因为80年代的香港电影圈里面有太多黑社会,我当时才十几岁,一个新人,别人不一定会听你的,但我又要坚持我的想法,所以蛮危险的。这个片子做出来的效果我也不太满意,我也知道我的个性蛮麻烦的,所以当时真的不太喜欢做电影,还是想去画画和摄影。
直到《胭脂扣》,我才开始对电影有点兴趣。因为《胭脂扣》里的每一段影片、每一个场景都做得很考究,整个氛围都做得很足,这样一来,整个时代就会出现,我很喜欢那种“把整个时代抓住”的感觉。
从那之后,我做得更加大胆,开始把我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解融入到电影美术里面。台湾一个做京剧革新的戏剧人吴兴国很喜欢我这种尝试,于是请我去台湾做一些戏剧的舞台美术。我就这样开始了七年在台湾的创作。那七年,我只做电影和戏剧的造型,全心研究全世界的造型艺术。不过,只做造型真的钱很少,当时我连助理都请不起。
到了台湾,我终于有机会重新去研究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因为香港这方面的文化环境不算特别好,当时内地也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所以我就在台湾做这方面的研究,每天去诚品书店买几万块钱的书搬回家,就那么疯狂。刚好又认识了台湾那批做电影的人,和杨德昌、蔡明亮、侯孝贤他们都变成好朋友,大家都对传统文化艺术有兴趣也有见地,一起交流都是很有力度的。
去为《卧虎藏龙》做电影美术是很顺其自然的,我在台湾早就认识了李安,他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找我去做美术,我就去了。当时我已经七年没有做过布景了,在这部电影里重新把布景做起来,后来就拿了奥斯卡最佳美术。好像突然从低谷走上巅峰,那段时间我蛮风光的,开始出书,摄影也重新拾起来了,法国、西班牙、波兰等等好多地方请我去做展览。

叶锦添
现在我不再局限于电影艺术了,虽然大众认识我是通过《卧虎藏龙》《无极》《夜宴》《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红楼梦(新版)》《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些,但我现在更多在用装置艺术的理念和方式来做舞台、做电影,我已经可以把这些东西换来换去,演化成好多种艺术形式,越来越得心应手。不过,大部分的作品来来去去都不会很商业的。
我的整个生命历程都在不断地把自己推到极限。去旅行也是一种把自己推到极限的方式,因为我意识到,我一直留在香港的话,看不到世界,一辈子都长不大。有段时间我想要突破自身的局限,就去全世界旅行一圈,回来后就发觉,现有的传统文化的确有很强的部分,但是比较缺乏当代的、前卫的部分,我们还是在用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很拙的那种人,看起来傻傻的,想事情的方式不是很正常,连去学校都不会走,不认识路,总是走错,我到现在也不能开车,我在跟人聊天或者演讲的时候,想法经常跳,我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也正因为我有这种拙,我才会在其他方面有一种灵气。
我不算是皈依宗教的人,但是我身上的确有某种神秘的东西,蛮奇怪的。他们都说我写的东西很宗教,包括我做服装,怎么决定一些细节,都没有什么原因的。我的哥哥身上有宗教的部分,但我好像没有。父亲过世的时候,哥哥就开始吃素了,等到哥哥决定出家的时候,我还不太懂宗教,那段时间他一直陪着我,也跟我长谈过。哥哥虽然出家了,但一直到现在,我每次做展览或者演讲他都会来看我,而且他很有兴趣跟我谈论艺术和宗教相关的话题。
到今天为止,大多数的电影美术都没有多大的自由度,只是一种模仿,没有精神性,也没有味道。其实全世界只有少数电影有精髓,我期待未来的电影会出现一个开放性的试点。所以我要去其他领域找寻力量,持续不断地让自己增强,懂得更多语言,掌握更多技术,获得更多经验,思考更多问题,再去做电影才会做出新的理解。人总是不能退后的,应该越来越强。
艺术应该有冒险性,有张力,不多不少地让人产生一种兴奋或者唤起一种升华。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艺术作品会感觉自己瞬间被震到,然后会有共鸣。艺术应该给人那种“震到”的效果,从而对观看者产生影响。
所有人都觉得你好,那没什么意思。所有人都喜欢你的作品,你的思维就过于稳定、过于贴近这个时代。艺术家应该走在时间的前面,领先甚至超前于时代。2019年应该做2025年的东西,即使有时候受众不那么接受。像新版《红楼梦》,因为曹雪芹营造的美是逝去的美,半虚半假,带着浓烈的神秘感与伤逝色彩,又有很重的象征色彩,所以我希望找一种中国的语言,尝试用中国的语汇、中国的节奏、中国的图案去呈现一种完全诗意的场景,不一定要写实,最后我用了戏曲的方法来处理。

叶锦添
永远都在挑战观众,作品才会是永恒的。我相信,时间越往后走,新版《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会出来的。把昆曲的方式用在影视剧中的做法,迟早有人来做,而且迟早会成功,我们将来还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作品。
我做作品不求当下的受众反应,我是撒种子的。有时候因为条件等因素,没有办法做到理想的样子,没有形成完整的美学语言,意味着没有成熟的文化性和艺术性,外界很难欣赏你,所以不是每一个作品都会像《卧虎藏龙》那么成功。但是,这些尝试和探索绝对是有意识的影响,我们真正想表达的已经在其中萌发。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看法,我们要敢于不跟随西方的美学体系。
在“新东方主义美学”里,我找到的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个源头。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航海历史、殖民地问题产生了文化断层,在马可·波罗之后,国外出现了东方主义,而中国慢了一步,因此我们现在做的很多是二手的东方主义,而且已经没办法贴合到如今这个时代。新东方主义不属于现在,也不属于未来,非常自由,可以创造更多可能性。我试图在数百年的断层中找回其间的演变痕迹和连接点,把我们以前的东西重新做回来,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适用于今天的新的美学语言,这是我的功课。
太多人愿意从众,愿意为了迎合市场而媚俗,所以我们做出来的很多东西并不动人。做艺术恰恰要保持一颗童心,干净纯粹,那才是艺术该有的样子。
有一些东西是未来需要的,就看时代有没有到来。时代到了,你会发觉,原来我们没有缺失。
但是,如果没有在时代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和积累,就算好时代来了,没有基础也不能做出与时间配套的艺术。所以,如果时代还没有来,我们就不做了吗?不可能。
从艺术层面看,还原或者逼真不是最重要的,神韵更重要。我们画人像的时候,通常会看到五官、看到光影,线条抓得很准确。百分之百的准确就不对了,画出来的好像不是眼前的人,因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还要加入某种真实感或者说熟悉感,让这幅画有神韵在里面。
我经常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现在我可能只做到了20%。我也知道问题在哪里,小时候可能是没有找到同类,长大以后发现这个时代太嘈杂太喧嚣,速度也太快,周围的声音让我的情绪没办法不受到干扰。很多时候我都没有满足感,越来越难以获得满足感。我还是喜欢独处,也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可惜的是,今天好多人甚至年轻人都好像没有我这么好奇了。我们应该做那种内心永远不会长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