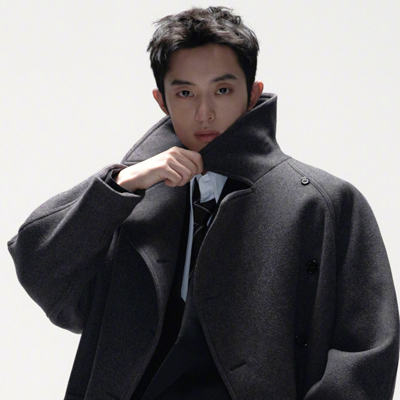“DIVA”一词可追溯至拉丁语“divus”(意为“神圣的”),最初用于形容被神化的古罗马君主。16世纪意大利歌剧兴起后,该词被赋予新含义——专指歌剧中的“首席女歌唱家”(prima donna),她们以高难度的花腔咏叹调(如莫扎特《魔笛》中的夜后角色)与戏剧张力征服观众,成为舞台的绝对灵魂。这些歌剧DIVA不仅是技艺的化身(如19世纪女高音玛丽亚·马拉布兰在《诺尔玛》中的精彩演绎),更通过华服珠宝与传奇人生,成为上流社会的文化偶像。
20世纪后,“DIVA”逐渐突破歌剧的界限。百老汇音乐剧《芝加哥》将“DIVA精神”与反叛女性叙事结合,塑造出Roxie(洛克希)这类“蛇蝎美人”形象;流行乐坛则借Madonna(麦当娜)、Beyoncé(碧昂斯)等巨星,将其定义为“舞台统治力与社会影响力兼具的女性艺术家”。词义也从单纯的“顶级女歌手”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既包含对卓越技艺的敬意,也暗含对“自我意识强烈、敢于打破规则”的女性特质褒贬不一的争议。
当我们尝试在华语乐坛中寻找一位最能诠释“DIVA”一词多重维度的歌手时,江映蓉与吴莫愁不约而同地提到了CoCo李玟,这也与我们的想法一致。CoCo李玟的音乐生涯横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既承载着传统天后的艺术高度,又打破了文化、语言与舞台表达的边界,并在舞台上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经典造型。正是出于这份不谋而合的敬意,我们最终让江映蓉与吴莫愁分别通过几组风格各异的主题大片演绎李玟在不同专辑的封面造型,传达对这位时代DIVA的真诚敬意。


想你的365天
1998年,李玟发行英文专辑Just No Other Way(《爱我别无他法》),全球销量突破200万张。这一数字背后,是华人歌手首次以全英文专辑叩击欧美主流市场的野心。两年后,她站上奥斯卡舞台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A Love Before Time”(《时间之前的爱》),成为首位在该颁奖礼上献唱的华人歌手。这一时刻的意义远超音乐本身——当她的声音穿透柯达剧院穹顶时,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隔阂似乎被短暂消融。
而在千禧年后的华语娱乐圈,李玟的舞台形象堪称一场“美学革命”。当多数女歌手仍以玉女形象示人时,她已穿着荧光短裙、顶着红色牛角头在“Di Da Di”的MV中热舞。这段被网友称为“滴答舞”的表演,以每秒3次的骨盆摆动频率挑战保守审美,却也因极强的感染力成为全民模仿的对象。
这种“破壁”意识同样体现在她的音乐创作中。2001年的《刀马旦》将京剧唱腔与嘻哈节奏交织,周杰伦的曲调遇上李玟的转音,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身段被解构成流行文化的视觉符号;《月光爱人》则以气声唱法勾勒出东方美学的留白意境,证明抒情歌曲不必依赖高音轰炸也能直抵人心。似乎在李玟的音乐基因中从来都不存在“安全区”,她总是在试探华语流行乐的更多可能性。
更深远的影响或许在于文化认同的重构。当李玟以小麦色皮肤、健美身材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时,她打破了华人女星以白皙纤瘦为美的单一审美体系;当她在BBC(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中强调“我的根永远在中国”时,又为海外华人提供了文化身份认同的范本。这种突破不仅关乎个人形象,更折射出全球化时代华人群体寻找自我定位的集体焦虑与希望。
2023年7月5日,李玟的溘然而逝令华语乐坛陷入一片静默。这位以“热力女王”形象烙印于时代的歌手,最终因长期受抑郁症的折磨选择结束生命,年仅48岁。然而,在她最后的舞台上,人们看到的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CoCo。这种“燃烧自己直至最后一刻”的舞台人格,恰是DIVA精神最极致的注解,而她的选择似乎也揭示出DIVA精神的悖论性内核——她们必须将个体的脆弱转化为集体的精神图腾。正如DIVA最原始的定义:拉丁语中的“神圣者”,注定要以破碎之躯,承载一个时代的星光。
CoCo,想你的365天里,愿你一切安好。


从“造神”到“共生”
纵观华语乐坛DIVA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性:她们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无论是用音乐突破文化隔阂,还是以形象映射社会思潮,每个时代的DIVA都在用独特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脉搏。
在冷战铁幕尚未完全消融的1970年代,邓丽君的歌声如同一股暖流,悄然融化着海峡两岸的文化坚冰。她的《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有宏大叙事,却以私密的呢喃重构了华人情感表达的范式——爱情不再是禁忌,而是可以公开言说的浪漫。
这种“温柔的革命”背后是惊人的文化穿透力。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磁带通过走私渠道传入中国大陆,青年们用布包裹着录音机秘密播放,工人、学生乃至知识分子在《何日君再来》的旋律中,触摸到久违的人性温度。
如果说邓丽君是月光,梅艳芳便是燃烧的火焰。1985年,她以《坏女孩》中的露脐装、烟熏妆和挑衅歌词震动中国香港乐坛。这首描述女性主动追求情欲的歌曲,不仅创下一周卖出72万张的纪录,更撕碎了传统“乖乖女”的刻板印象。
但梅艳芳的DIVA特质远不止于反叛。在《女人花》的低回婉转中,她将自身情路坎坷与抗击子宫颈癌的隐痛融入演唱,让“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成为万千女性的命运共吟。2003年,她身披婚纱举办了告别演唱会,更将这种悲情升华至哲学高度——当她说“我把自己嫁给了音乐”时,一个DIVA的职业生涯与生命终章完成了重合。
1996年,王菲在专辑《浮躁》中几乎包揽了所有词曲创作,迷幻电子音效与封面上的晒伤妆,彻底颠覆了“天后”的定义,也标志着DIVA从“大众情人”向“独立艺术家”的转型。她的“冷调DIVA”形象体现在多重矛盾中:在北京胡同倒痰盂的世俗画面,与《重庆森林》里吃凤梨罐头的文艺女神形象交织;《红豆》的普世柔情与《开到荼蘼》的虚无主义并存。这种拒绝被定义的姿态,恰恰契合了1990年代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新兴中产阶层的身份焦虑——他们既渴望个性表达,又困于现实桎梏。
进入千禧年,郑秀文用高跟鞋踩出了另一条DIVA之路。在《终身美丽》的歌词“任她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中,她将都市女性的自我救赎唱成时代金句;《眉飞色舞》的电子舞曲风则与中国香港经济复苏期的享乐主义产生共鸣。
但她的真正突破在于“不完美”的真实性。2019年经历抑郁症后,她在红馆演唱会含泪唱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台下万人打开手机电筒回应,这种从“精致天后”到“伤痕讲述者”的转变,让DIVA精神转化为普通人的生存勇气。
而当时代迈向当下,当社交媒体将舞台延展至每个人的手机屏幕,当流量算法不断解构传统的权威叙事,DIVA的定义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重构。新一代观众不再满足于仰望“完美女神”,而是渴望在共鸣与互动中,与偶像共同书写这个时代的生存答案。社交媒体时代的DIVA们主动撕去“神性”标签,将皱纹、崩溃与迷茫纳入公共叙事。这种“瑕疵美学”并非人设坍塌,而是以祛魅的方式重构偶像与大众的关系:DIVA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容器”,而是与普通人共享生命经验的“同行者”。
那么,下一个DIVA会是谁?
答案也许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个歌者与听众共同呼吸的瞬间。正如梅艳芳《夕阳之歌》里所唱:“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DIVA们以生命诠释刹那的璀璨,而那些曾被DIVA之光照亮的人,终将学会在黑暗中哼唱自己的光。
江映蓉:一路皆是风景
曾经是风光无两的冠军艺人,也因为整容争议在泥潭中挣扎,如今的江映蓉在身体的自律中感受到精神的自在与安定。路上经历的那些好与坏在此刻的她看来,皆是风景。

江映蓉
刚刚好
2024年10月,江映蓉全程参与录制,并担任制作人的综艺节目《骑时刚刚好》播出了。“它也可以叫做’其实刚刚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住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一位朋友曾提议一起去感受天安门广场,于是江映蓉买了一辆自行车,想试试新的运动。“没想到我可能是有点儿天赋的,也不累,还能晒晒太阳,就喜欢上了。”节目中,她与好友从家乡成都出发,在川西的乡村公路上用刚好可以欣赏到风景的速度驰骋,也在落日的山脚下跟着音乐随性起舞。网络上那些新的或旧的流言蜚语,似乎都与这个自由的女生毫无关系。

江映蓉
提到江映蓉,健与美的印象总是立刻与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她是内地娱乐圈少有的唱跳俱佳的动感女艺人。台下的她热爱运动,无论是骑行、力量训练还是马拉松和攀岩,她都乐于尝试,运动在这些年已经成为音乐之外的另一种日常。如今,开始创业开公司的她自然而然地把运动作为职业新阶段的重要元素。“音乐和体育都是与心率有关的,它们都是一种节奏。为什么健身房都有音乐,它是在激励你进入一个状态。体育当中也有舞蹈,因为舞蹈也属于体育,可以强身健体,它们是完全可以融合的新型生态链,这是我想探索的方向。”

江映蓉
去年是江映蓉出道的15周年。2009年,她顶着《快乐女声》选秀总冠军的耀眼光环出道,许多歌迷陪伴她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从青涩冲动到成熟稳重。然而,在她于成都举办的“Flower Life音体融合实验场”出道15周年个人演唱会上,她将现场变为一个巨大的运动场,融入动感单车等健身元素。台下的观众们仿佛恍惚间回到了那个疯狂的夏天,和她一起挥洒汗水,蔓延纯粹的快乐。15年,对于一位歌手来说,是不算短的职业生涯。令人意外的是,这次演唱会竟是这位名字几乎令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冠军音乐人的首次个唱。“从音乐角度讲,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别人的歌的。首先对于我的听众不是很好,毕竟如果你在没有那么多作品的情况下开很多演唱会,是不是有一点消费他们?”

江映蓉
曾经,江映蓉收到过一些来自歌迷的信件。在这些信中,常常有歌迷和她说,自己在某个人生阶段非常抑郁,甚至想要放弃一些东西时,因为听了她的歌受到鼓舞,从而坚持了下来。而她自己也曾陷入抑郁状态,在音乐中调整自己,和自己对话。“这些故事让我理解他们,同时也更理解了我自己。我想更尊重我的歌迷,因为他们会在我的音乐中寻找到力量,这是我作为歌手的一个非常大的使命感。”

江映蓉
快乐不快乐
江映蓉幽默地说,自己的音乐梦从妈妈的胎教时期就开始了。妈妈很喜欢音乐,尤其爱听Shirley Temple(秀兰·邓波儿)的歌曲,而她在4岁时就能对Whitney Houston(惠特妮·休斯顿)的许多名曲倒背如流。“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原来音乐这么迷人!”家里人会因她对音乐的热爱而鼓励她学习舞蹈、唱歌,也不会因为她学习不好而责备年幼的她:“我们家里的教育是,你不要中不溜,因为你是一个很独特的人。所以你可以当倒数第一,也可以当正数第一,哈哈哈哈哈。”

江映蓉
出生在80年代的江映蓉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自我”对她而言似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然而,在她成长的年代,华语流行音乐似乎在经历一个属于都市情歌的潮流,统一的芭乐旋律之下,女歌手们倾诉着自己的情伤和对爱情的渴望。“让我感觉都是女生很‘小’,男生很‘大’。”这时,李玟的出现让她觉得耳目一新:她开心地在镜头前舞动,无忧无虑地表达着自我,愉悦地享受舞台。“那个状态其实影响了蛮多女孩子对‘爱自己’的一个重新认识。但是很多歌都在唱‘我永远爱你’,没有你我就会怎么样。但是李玟告诉我们,不一定需要一个男性来爱你,或者有个家庭才是女性的归宿。”

江映蓉
李玟对自己所热爱的音乐投入的热情、忠实和坦诚成为江映蓉对音乐和舞台执着追求的最初的动力。在那个“Diva”还没有成为一个高频形容词的时代,江映蓉将李玟当作偶像,在精神上追随着这位“大女主”,将每一个音符和动作都打磨到极致。“我觉得Diva是把她的事业当作修行的,把音乐当作生命的乐章去谱写。”拍摄当天,江映蓉和我们分享她的早餐:“两个鸡蛋,一份面条,一份150克的蔬菜。”她的自律令人惊叹,就像她在舞台上呈现的那些完美定格。她希望自己的舞台人格和生活人格是一体而不是割裂的,那些日常中所坚持的自律和极致最终都会在舞台上绽放光彩,而“自律”才是一位Diva的灵魂。

江映蓉
如今,身体的自律带给江映蓉的是平静:她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她在社交媒体上自洽而自信地展示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扭捏和遮掩,也不会刻意地博人眼球。在她的全新专辑Flower Life(《新生之花》)中,以往热辣惹火的江映蓉将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节奏暂时放缓,在更加灵动的器乐和玲珑婉转的丛林节奏中歌颂一种更加气定神闲的生命力。专辑封面上,她身着金色的金属质感上衣,在一片蓬勃的植物中端坐,没有过多的强调与矫饰。曾几何时,她是舞台上的绝对主角,所有的镁光灯都照射在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身上;如今,她则主动退后一步,在更多“枝叶”的衬托和露水的滋养下,蓬勃生长。

江映蓉
“我的想法是要成为一个幕后推手,我希望能够让人看到更多元化的音乐。现在音乐太贫乏了,特别是对于大众听歌来说可能是抖音居多,或者是哪个火玩哪个。但其实音乐本身不是这样的,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东西,就像一个人怎么可能只有快乐?所以它一定是丰富的。”
吴莫愁:快乐不需要理由
吴莫愁经历过出道即爆红,也经历过疲惫消沉的人生低谷。在偶像的影响下,她曾努力微笑,全力燃烧自我;如今,依然是音乐与偶像令她找回自信,发自内心地快乐与微笑。

吴莫愁
热烈地活着
2025年伊始,东北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吴莫愁新专辑的先行曲《东北》在全网发布了。一颗咬了一口的冻梨包裹在东北大花餐巾里,被一双玉手托在手心,这一幕竟让人一时模糊了《白雪公主》和东北文艺复兴的次元壁,热烈,还有点儿癫。前几年,吴莫愁因创造力的枯竭和对音乐的疲惫从聚光灯下隐身,回到了家乡齐齐哈尔。“那是很珍贵且无法复制的一个经历,可能人生中也只有在那个时刻才能有这样的决定,回到家乡去感受生活。”齐齐哈尔的天总是那么蓝,空气中透着凛冽的味道夹杂着淡淡的冰沙般的甜,晚上则是烟熏调的烧烤味。相熟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会在早市儿偶遇,互相寒暄。

吴莫愁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心愿,希望自己可以有一首赞美家乡的歌,也希望里边有我成长的一些影子,算是自我情怀的一种记录。”吴莫愁以“铁锅炖”一般的杂烩方式把自己喜欢的风格糅在一起:说唱、Trap(陷阱音乐)、地方传统器乐、摇滚……“这是我善于和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对她来说,复杂成为另一种简单。从出道起,“吴莫愁”三个字似乎就代表了一种音乐和视觉上的极繁主义,她在声音中加入的那些转音、嘶哑,她在脸上叠加的飞扬妆容,在她出道的那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带着一种不自知的Camp(坎普)。在人生低谷被家乡的点滴所治愈,回到音乐世界的她似乎找回了那种不在意别人眼光的“自我”。

吴莫愁
很长时间以来,吴莫愁会经常练习在舞台上屏蔽杂念。回来之后,面对这个依然能量爆炸的场域,她更加专注,也更懂得享受了。2023年,出道满十年的她终于决定做一次自己的巡演“YES MO LOVE”。她说,这是她给自己的一个音乐成人礼。“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没准备,2023年的时候我觉得时间到了。”她自认是个人来疯,面对台下的乐迷,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魔性一股脑释放出去,碾压整个现场;同时,她也感受到乐迷汹涌的情绪,观众的温度,甚至观众流的汗,观众的眼神,“他们恨不得把自己烧掉的那种爱,你都是能感觉到的”。

吴莫愁
对于这个在刚刚出道就体验过“爆红”的女孩儿来说,成功的定义似乎从来不是名与利,她希望在舞台上让观众觉得自在、舒服,体验一场美妙无比的表演。就像她的家乡,虽然身处极北边陲,却永远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我给观众的一种刺激和感受,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玩的瞬间。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无论给观众带来惊喜、惊讶还是惊吓,我都觉得只是一个好玩的存在。唱歌好的人很多,我希望我是特别的一个,让观众体验活着的热烈。”

吴莫愁
纯粹地享受微笑
“我觉得她的表演是能够特别沉浸的,一下就抓住观众的眼球,把人吸进去的那种感觉”。吴莫愁对于Diva的定义像极了她自己。2012年,她就是这样用一首“Price Tag”(《价格标签》)抓住了全国观众的眼球。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吴莫愁的少女时代与当下的她截然相反,那时的她性格内向。她会安静地在音像店驻足许久,看着里面的CD、磁带,听里面放的流行音乐。

吴莫愁
后来,爸爸给她买了一台粉色的录音机,她也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张磁带——李玟的《爱琴海新歌+电音精选》。“买回去我就放进录音机里,一下子就呆住了,我说我天,这是什么音乐!后来我买了好多CoCo的专辑,我特别喜欢《Baby对不起》《第九夜》这种有律动感的。后面又去买她的VCD,又被惊呆了,我说我天,这是什么舞蹈!”李玟的出现仿佛按下了吴莫愁体内分泌多巴胺的开关,想到李玟,她就会不由自主地嘴角上扬,仿佛这个名字可以把她全部的快乐调动起来。

吴莫愁
2022年,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上,吴莫愁通过现场连线向李玟表白,那是她离偶像距离最近的一次。她觉得这样的距离刚刚好。2024年,海南电影节上,吴莫愁获邀演绎李玟的《自己》;而三年前的同一个舞台上,偶像也曾唱过同一首歌。

吴莫愁
来到海南的前一天,她恰好在成都做江映蓉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的嘉宾。“晚上的时候,我同事突然跟我说,有一位杂志的编辑想要见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礼物要给我。”那天,吴莫愁收到了一张来自李玟的to签专辑。原来,这位编辑曾在采访李玟时问到她对于喜欢她的新生代音乐人的看法,李玟特意准备了这些专辑,拜托编辑将这些专辑转送给音乐人们。

吴莫愁
“对于我来说,这真的是突如其来的惊喜和感动,刚好第二天我就要去海南演唱CoCo姐的歌。我一直相信音乐能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幻想,而且它们最终都成了现实。”
出品:李晓娟 / 监制:滕雪菲
江映蓉:一路皆是风景
策划:蘑菇仙 / 摄影:Adon / 撰文:张林鑫 / 妆发:丹帝 / 造型:Jade / 创意:徐若昕Raw(ADVC) / 美术:温方宇H.U.A(ADVC)、李泽豪(ADVC) / 修图:子鉴 / 摄影助理:小宇 / 策划助理:Scarlett / 影棚:YEP studio(有了!影棚)
吴莫愁:快乐不需要理由
策划:蘑菇仙 / 摄影:Abo左多寶 / 撰文:张林鑫 / 妆发:K.Kay / 造型:Jingjing / 摄影助理:蓝鲸 / 策划助理:Scarlett / 影棚:YEP studio(有了!影棚)